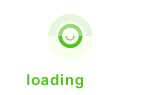本报记者 牛喜林
辛安亭(1904—1988)当代著名的教育家、出版家。山西离石县人,1931年考入北大历史系。1938年奔赴延安,到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编写教材。1949年,随军到西安、兰州,作为军管代表,接管了陕西师大、兰州大学、西北师院等高校,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、甘肃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、省文教厅厅长等职。1951年,调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社长、副主编。1973年,担任了兰州大学党委副书记、革委会副主任,“文革”结束后主持兰大工作,直到1984年。
新中国教材编写开拓者
辛老一生从事教材编审工作,专门从事教材编写就有22年,其中在延安11年,在人民教育出版社11年,是新中国教材编写的开拓者。而在延安的11年是辛安亭最为惬意的时光。
1938年,辛安亭奔赴延安参加革命,在陕北公学学习了一段时间后,就被分配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教材编审科工作。当时,陕甘宁边区学校沿用的仍是国民党政府的课本,不仅知识陈旧,远离现实生活,而且思想落后,充满了封建糟粕。配合当时的抗日形势,辛老从教材内容到编排体系进行了大胆革新,全身心地投入到教材编写工作中。当时编写教材的同志共4人,同住在一孔窑洞里,除了集体讨论外,白天各写各的,很少说话。晚上一直写到11点钟,天天如此,只感到愉快,不知道疲倦。他们编写的小学语文、历史、地理、自然等解放区最早而有系统的新型课本,对解放区的普通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。同时,辛老根据农民、干部学文化的需要,编写了儿童读物、民众识字课本、工农干部识字课本及《新三字经》、《日用杂记》等。辛老在延安共编写小学课本及各类读物40余本。一度他的知名度非常高,以至于人们说,“政府的林主席,编书的辛安亭”。
1951年秋,根据全国中小学生的实际需要,中央决定成立人民教育出版社,辛老作为著名教材编审专家,调任出版社副社长、副总编,主持出版社工作(教育部副部长叶圣陶兼任社长、总编)。辛老与叶老密切配合,深入调研,从全国各地抽调各学科专家,共同编写新中国第一套中小学教材。他反复强调,这种教材必须具备三个特点:一是要“新”,即要吸收文化科学的最新成就,不断更新过时的东西;二是要“精”,即在保持本学科必要的完整性、系统性的前提下,抓住基本概念、基础知识,讲深讲透,不可贪多求全;三是要“清”,即要写得清楚明白,简洁易懂。1956年,新中国第一套统编教材全部出版,为新中国普通教育做了奠基性的工作。
两次受命进兰大
辛老曾两度主持兰州大学工作,都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。解放初期接管的是国民党管理多年的旧大学,敌我之间、新旧势力和新旧思想之间,斗争十分尖锐。辛老按照“逐渐改革,稳步前进”的方针,妥善地处理了各种复杂问题,既发挥了积极分子的作用,团结了大多数教职员工,并与国民党特务等敌人进行了坚决斗争,短短几个月,就在兰大建立了新的管理制度和正常的教学秩序。“文革”期间,辛老受到诬陷和迫害。1973年,辛老被任命为兰州大学党委副书记、革委会副主任,但实际工作仍受极“左”路线的干扰。在狂风恶浪中,他始终稳重自持,坚贞不屈,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。1976年,辛老被任命为兰州大学党委副书记、副校长,再度主持兰大工作(书记、校长缺位)。兰大在“文革”中是遭到严重破坏的“重灾区”,粉碎“四人帮”后,辛老以古稀之年主持兰大工作。他积极整顿干部、教师队伍,整顿教学秩序;落实知识分子政策,为一大批多年蒙冤的干部、教师平反昭雪,使他们重新返回工作岗位。几年功夫,兰大工作重点很快转移到以教学和科研为中心的正确轨道,为兰大在新时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一生清廉无私欲
1953年中央机关精简人员,辛老作为人民教育出版社主持工作的副社长,首先把红军时期就参加革命的夫人精简回家,直到80年代才按党的有关政策恢复了她的干部身份,落实了老干部身份。辛老唯一的女儿大学毕业后,被选中到一所大学任教,但那所大学提出交换条件:调一个工人到兰大去。辛老断然拒绝,结果女儿去了一个单位做野外工作。在辛老身边长大的孙女,在兰大上学时成绩优秀,毕业时很想留在兰大,但辛老得知系里暂不急需,也就作罢。孙女说:在爷爷奶奶营造的革命家庭氛围中,着实领会了规规矩矩做人、凭本事吃饭的道理。
解放初期,他担任军代表、厅长,组织上给他安排了一个排长当警卫员,但他常常一个人步行外出。警卫员找不到他,十分着急,很有意见。他解释:我找教授谈话,你挂着手枪站在门口,不是让人家害怕吗?司机也有意见:首长每次出去都不叫车,既费时间又不安全。辛老解释:安步当车也是我的一种锻练方式。国家按规定给辛老配备了专车,但他在用车上公私分明,他的女儿上学与他上班同一方向,他也不肯顺路把女儿捎上。1982年冬天,一位教师去看望辛老,辛老患感冒要去医院打针,这位教师劝他:“到医院天气冷,打个电话请护士来家打吧。”辛老说:“不。医院打针的人很多,护士很忙,我还可以走。”这位教师搀扶辛老到医院后,辛老不声不响地排在候诊队伍后面。
重才、惜才受爱戴
提起辛老,留美电化教育专家南国农敬佩之情油然而生。他说:我一生最崇敬的有两个人,一个是陶行知,一个是辛安亭。对学生,我经常引用以辛老为原型总结出来的做人行为规范:对他人和同事,多一点尊重,少一点苛求;对社会和集体,多一点奉献,少一点索取。
南国农深情地说:辛老是一个忠厚、正直的学者,也是一个有胆有识、无私无畏的人。辛老在组建甘肃教育学院时,从其他高校调去的教师中,有几个人是“右派分子”、“反动学术权威”。辛老不仅安排他们上课,而且处处关心他们。当时我只身一人在兰州。一次,我患胃溃疡摔倒在地,磕破了头,满身是血。辛老听到后,立即叫校医室主任亲自为我医治。他要夫人为我拆洗血衣,并多次给我送饭。我当时是个“右派”,一般人都躲着我,而辛老却这样体贴我、爱护我。这在当时是要担风险的,但辛老考虑的是学生的利益,而从不考虑个人的得失,所以无私、无畏。在“文革”中,曾有造反派以此发难,批斗并质问他:为什么要引进并重用牛鬼蛇神南国农?辛老回答:南国农是我引进的,但并没有重用。南国农说起这事,总是禁不住流下感激的眼泪。他说,其实我是另一位副院长要去的。但辛老不仅自己承担了责任,而且敢于向造反派说“不”。
在甘肃教育学院创业的艰难岁月里,教师们都说,在辛老领导下工作,心情舒畅。现河西学院教授、当年的助教向叙典是位单身,春节没回家探亲。大年初一,辛老亲自登门拜年。望着老校长,听着他问候的话,像一股暖流注入年轻教师向叙典的心田,向叙典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。
辛老为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殚精竭虑,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。他的精神境界、人格魅力和学术财富,将永为教育后辈汲取和发扬。
《中国教育报》2005年3月5日第4版
(网络编辑:李媛)